- 文本
- 历史
[3] Perhaps ten years later,after p
[3] Perhaps ten years later,after playing jazz with black musicians in various Harlem clubs, hanging out uptown with a few young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I began to learn from them something of the extraordinarily varied and complex riffs and rituals embraced by different people to help themselves get through life in the ghetto. Fantasy of all kinds--from playful to dangerous-- was in the very air of Harlem.It was the spice of uptown life.[4] Only then did I understand the two shoeshine men. They were trapped in a demeaning situation in a dark corner in an underground corridor in a filthy subway system.Their continuous staring off was a kind of statement, a kind of dance. Our bodies are here, went the statement,but our souls are receiving nourishment from distant sources only we can see. They were powerful magic dancers, sorcerers almost, and thirty-five years later I can still feel the pressure of their spell.[5] The light bulb may appear over your head, is what I'm saying, but it may be a while before it actually goes on. Early in my attempts to learn jazz piano, I used to listen to recordings of a fine player named Red Garland, whose music I admired. I couldn't quite figure out what he was doing with his left hand, however; the chords eluded me. I went uptown to an obscure club where he was playing with his trio, caught him on his break,and simply asked him."Sixths," he said cheerfully. And then he went away.
0/5000
[3] 或许十年后,在哈莱姆各个俱乐部和黑人音乐家一起演奏爵士乐,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上城闲逛后,我开始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不同人所接受的异常多样和复杂的即兴演奏和仪式帮助自己度过贫民窟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幻想——从好玩的到危险的——都弥漫在哈莱姆区的空气中。它是住宅区生活的香料。<br>[4] 那时我才明白那两个擦鞋的人。他们被困在肮脏的地铁系统地下走廊的一个黑暗角落里的一个有辱人格的境地。他们不断的凝视是一种陈述,一种舞蹈。声明说,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但我们的灵魂正在从只有我们才能看到的遥远来源接收营养。他们是强大的魔法舞者,几乎是巫师,三十五年后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咒语的压力。 [5] 灯泡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头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亮起。在我尝试学习爵士钢琴的早期,我曾经听过一位名叫 Red Garland 的优秀演奏者的录音,我欣赏他的音乐。然而,我无法弄清楚他用左手在做什么。和弦避开了我。我去了住宅区的一个不起眼的俱乐部,在那里他和他的三人组一起玩,在他休息的时候抓住了他,简单地问他。“六分之一,”他高兴地说。然后他就走了。
正在翻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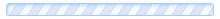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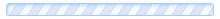
[3] 也许十年后,在哈莱姆区的各个俱乐部与黑人音乐家一起演奏爵士乐,与一些年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住宅区闲逛之后,我开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不同人群为帮助自己度过贫民区生活而采用的异常多样和复杂的即兴演奏和仪式。哈莱姆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幻想——从嬉戏到危险——这是住宅区生活的调味品。<br>[4]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那两个擦鞋匠的意思。他们被困在肮脏的地铁系统地下走廊的一个黑暗角落里,陷入了一种贬低的境地。他们持续的凝视是一种陈述,一种舞蹈。声明说,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但我们的灵魂正在从只有我们能看到的遥远的源头获得营养。他们几乎都是强大的魔法舞者和巫师,35年后,我仍然能感觉到他们施咒的压力。[5]我想说的是,灯泡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头上,但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继续。在我尝试学习爵士乐钢琴的早期,我曾听过一位名叫红加兰的优秀演奏家的录音,我很欣赏他的音乐。然而,我不太明白他左手在干什么;我听不见和弦。我去了住宅区的一家不知名的俱乐部,在那里他和他的三人组一起玩,在休息时抓住了他,简单地问了他一句,“六分之一”,他高兴地说。然后他就走了。
正在翻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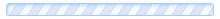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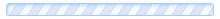
[3]也许十年后,在哈莱姆区各种俱乐部与黑人音乐家一起演奏爵士乐,与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起在住宅区闲逛之后,我开始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不同的人所接受的极其多样和复杂的即兴重复和仪式,以帮助自己度过犹太区的生活。哈莱姆区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幻想——从顽皮到危险。这是住宅区生活的调味品。[4]这时候我才明白这两个擦皮鞋的人。他们被困在肮脏的地铁系统的地下走廊的一个黑暗角落里,处境十分恶劣。他们持续的凝视是一种陈述,一种舞蹈。我们的身体在这里,声明说,但是我们的灵魂从只有我们能看到的遥远的地方接受营养。他们是强大的魔法舞者,几乎是巫师,三十五年后我仍然能感受到他们咒语的压力。[5]我想说的是,灯泡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头上,但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开始。在我尝试学习爵士钢琴的早期,我经常听一位名叫瑞德·加兰的优秀演奏者的录音,我很欣赏他的音乐。然而,我不太明白他用左手在做什么;我听不懂这些和弦。我去了住宅区的一个不起眼的俱乐部,在那里他和他的三人组一起玩,在他休息的时候抓住了他,简单地问他。“第六,”他高兴地说。然后他就走了。
正在翻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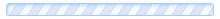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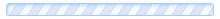
其它语言
本翻译工具支持: 世界语, 丹麦语, 乌克兰语, 乌兹别克语, 乌尔都语, 亚美尼亚语, 伊博语, 俄语, 保加利亚语, 信德语, 修纳语, 僧伽罗语, 克林贡语, 克罗地亚语, 冰岛语, 加利西亚语, 加泰罗尼亚语, 匈牙利语, 南非祖鲁语, 南非科萨语, 卡纳达语, 卢旺达语, 卢森堡语, 印地语, 印尼巽他语, 印尼爪哇语, 印尼语, 古吉拉特语, 吉尔吉斯语, 哈萨克语, 土库曼语, 土耳其语, 塔吉克语, 塞尔维亚语, 塞索托语, 夏威夷语, 奥利亚语, 威尔士语, 孟加拉语, 宿务语, 尼泊尔语, 巴斯克语, 布尔语(南非荷兰语), 希伯来语, 希腊语, 库尔德语, 弗里西语, 德语, 意大利语, 意第绪语, 拉丁语, 拉脱维亚语, 挪威语, 捷克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 斯瓦希里语, 旁遮普语, 日语, 普什图语, 格鲁吉亚语, 毛利语, 法语, 波兰语, 波斯尼亚语, 波斯语, 泰卢固语, 泰米尔语, 泰语, 海地克里奥尔语, 爱尔兰语, 爱沙尼亚语, 瑞典语, 白俄罗斯语, 科西嘉语, 立陶宛语, 简体中文, 索马里语, 繁体中文, 约鲁巴语, 维吾尔语, 缅甸语, 罗马尼亚语, 老挝语, 自动识别, 芬兰语, 苏格兰盖尔语, 苗语, 英语, 荷兰语, 菲律宾语, 萨摩亚语, 葡萄牙语, 蒙古语, 西班牙语, 豪萨语, 越南语, 阿塞拜疆语, 阿姆哈拉语, 阿尔巴尼亚语, 阿拉伯语, 鞑靼语, 韩语, 马其顿语, 马尔加什语, 马拉地语, 马拉雅拉姆语, 马来语, 马耳他语, 高棉语, 齐切瓦语, 等语言的翻译.
- 是镀金 含金量比较少
- 我们应该尽力去保护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
- 业务集中度向上;测量经验积累;能力提升
- 发夹发箍
- 吉祥如意
- Công việc làm thuốc nhuộm từ chàm diễn r
- 如果是DHL大约7-10天就可以到达欧洲
- Flugzeugbestand und Bewegungsmeldungen
- BeneCuando Costa tutto
- Ngoài ra, các địa phương còn tổ chức phu
- كان صديقي فرحا جدا في الحفلة
- 今天比昨天热
- 浅蓝色~常规款
- 你身高体重多少呢
- What is the law of the lever?The law of
- 我会给您发快递,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您可以货到付款,快递是免费的,我会提前支付运费
- Эрх шилжүүлэх гэрээ хүчин төгөлдөр болсо
- 你要干什么?
- حصل لنا الشرف
- 庄立鹏
- 你想要多少数量呢
- 今天比昨天热
- 先生今天购买我们还有很多小礼品哦
- 产品款式、厚度,材料你知道吗,以及你采购的成本
![[3] Perhaps ten years later,after playing jazz with black musicians in的简体中文翻译](http://wwwimg.woaifanyi.com/_data/woaifanyi_com_www/pic/logo.gif?v=81c5e4c6899453cc_2408)
